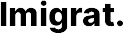大不列滇人山滇之城41 min read·Sep 4, 2018--
1
Share
大不列滇人,又稱雲南人、滇人。(英語:Diantnese or Yunnanese.)。主要包括今天在雲南以及緬北、四川涼山地區出生的居民。包括滇境內的上江人(“雲南漢人”)、彝人、白人、傈僳人、景頗人、潘泰人(“雲南回人”)、泰人(傣人)、瑤人、苗人、拉枯人等民族。以及在境外說滇語(雲南話)的僑民。在泰國,當地泰人把同樣是操粵語、潮汕語的來自廣東等地的僑民稱為“Chin”,把從雲南來的操雲南話的包括潘泰人(雲南回人)在內的所有滇人移民移民統稱為“Haw”,有的文獻中也拼寫為“Hor”或者“Ho”。當代雲南民族主義者稱呼雲南為大不列滇(The Great Diantnam)、滇尼亞(Diannia)或滇蘭(Dianland)
一、古滇文明歷史
(一)方國時代
古滇文明的開始非常早,從史前時代就已經開始了。至於它的結束時間,可以定在古滇作為一個文明賴以生存的整套政治、宗教、文化系統滅亡之時,也就是1382年明帝國攻滅大理的時刻。但是古滇文明的餘波,其實是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最後一批土司被消滅時,才徹底終結的。雲南所在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的,它正好處在幾個文明之間的十字路口。它的北面,是橫斷山脈中南北走向的通道,一直連接到內亞,這些通道被稱作“藏彝走廊”。它的東面,有西江流域,與南粵相連,可以與百越人發生聯繫。雲南本土有幾條河流,從雲南起源,一直流到東南亞,一條是流到越南的紅河;一條是瀾滄江、進入泰國後變成湄公河;一條是怒江,進入緬甸後變成薩爾溫江。向西,雲南與印度有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經過滇緬邊境的高黎貢山,通過緬甸一直延伸到印度,這就是有名的“身毒道”。在滇史上,內亞人通過橫斷山脈上南北走向的走廊、百越人溯江西上,多次向滇輸入人口和秩序。印度文明則通過身毒道向滇輸入文明和秩序。東南亞則是接受滇輸出秩序的地方,因為滇人可以順幾條河流而下,進入泰國和緬甸。
滇本土也是可以分成幾個區域的。首先是滇西北麗江一帶,這裏比較靠近吐蕃,在文化上和吐蕃比較相似,曾在吐蕃的封建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南部、東南部靠近東南亞的地方,離西江比較近,當地人的百越血統與特點比較濃厚。而在廣大的中部,以滇西的大理、滇東的昆明為兩個中心,這裏是滇的本部,屬於雲貴高原的一部分。這裏的海拔一般都有兩千米左右,有許多山,在山之間分佈著許多平坦的土地,一東一西還有兩個大湖,分別是昆明邊的滇池、大理邊的洱海。在群山與湖泊之間,有細碎的小塊平地,這種地形被叫做“壩子”。如此破碎的地形表明,若沒有外來大一統勢力干涉的話,雲南是很難形成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權的。
上古時代的雲南居民,和夜郎、巴蜀的百濮差不多,有自己的部落組織。通過橫斷山脈上的藏彝走廊,他們能夠跟內亞族群有充分交流。周朝消滅商朝的戰爭中,有許多內亞和百濮部族曾做為周的盟友參戰,古滇的部族很可能就參加過這次戰爭。西元前8世紀以後,斯基泰人在內亞興起,他們在之後的五百年間,通過藏彝走廊不斷進入雲南,這就形成了雲南境內越靠北、內亞血統就越多的人口分佈結構。內亞部族在滇西,形成了哀牢和昆明這兩個邦國。哀牢和昆明,與其說它們是國,不如說它們是部族聯盟。在滇中洱海附近的平原地區,有古印度人遷入,建立了白崖國(又名白子國)。在滇東,百越人順水西上,在西元前3世紀左右進入雲南,在滇東的滇池邊建立了滇國。滇國君主,據說是楚國的百越人將領。但是,滇國的武士集團中有很多內亞人。因此,滇國的統治階層應該是百越人加內亞人,兩者一起對被征服的百濮人進行統治。
在西元前最後三百年,雲南通往印度的商道已經非常繁榮了,有印度僑民出現在滇西。巴蜀、雲南的貨物通過身毒道沖過緬甸到達印度,一直到達今天的阿富汗一帶。這個時期,古滇文明的一些基本特質已經出現了。首先,是雲南和印度間緊密的聯繫。第二,就是雲南在地理、文化上的二元性,滇東、滇西是相當不一樣的。第三,就是古滇文明強大的內亞性。此後,在古滇文明的統治階層和武士中,內亞人一直是占主流的。第四,古滇統治階層中的百越因素,也在這時出現了。後來,滇東南的句町國,就是百越人建立的政權。在漢武帝入侵雲南時,滇國被征服,句町國強大了起來,白子國則繼續保持獨立。這樣,百越系居民主要在南、內亞系居民主要在北,這樣的格局就定型了。
(二)南中大姓
經過新莽和東漢的不斷進攻,上述幾個邦國都被毀滅了。但是,雲南本身的文明並沒有斷掉。像昆明國這種所謂的國家,本來就是部落聯盟,東漢打垮了它的國家組織,不過是使它變回部落狀態。漢帝國為了控制雲南,將大批各地土豪大族強制移民到雲南。漢帝國這樣做的本意,無疑是一箭雙雕的,一方面可以靠外來移民壓制雲南土著反抗、一方面可以借此流放帝國各地土豪。然而,這些大族的土豪性本來就是比較強的。比如南越國丞相呂嘉的家族,就是這樣一個大族。他們的共同體進入雲南後,和本土部落進行了俄充分的融合,雙方的習慣法慢慢對接在了一起。這些大族,比如呂嘉的家族移民到雲南後,完全有可能按照在南越國中家族的方式重建共同體,然後和本地部落通婚、博弈,雙方漸漸融合在一起。這些被強制移民的人,許多人本來就是被漢帝國剛剛征服的族群中的土豪,他們和雲南土著部落,在文明季候上是差距不太大的,他們的習慣法是比較容易對接的。習慣法,是可以不斷生長和融合的。比如,英國的習慣法,就是多個族群在不同時期加入自己的習慣法,融合、博弈的產物。當時的雲南,也出現了不同族群的習慣法相融合的情況。這樣,在相當於東漢晚期的時候,雲南進入了大姓政治時代。
所謂的大姓,到底是什麼呢。在2世紀的時候,雲南出現了十幾個大姓。這些大姓,大部分看上去很像漢姓,但也有的姓非常特別,比如很有名的爨(cuan4)氏。此外,比較有影響力的還有孟氏和霍氏。這些人一般都自稱祖先來自中原,但他們到底是不是所謂的“漢人”,其實是很難講的。首先,那些大姓領袖往往會和雲南土著部落通婚,雙方親如骨肉。當有移民違背了漢帝國的武斷法律,遭到緝捕時,土著往往會包庇他們。在土著當中出現糾紛時,這些大姓領袖也能嫺熟地運用雲南本地習慣法去進行裁斷。這種習慣法,被漢朝人稱作“夷經”。既然這些大姓懂得“夷經”,土著遇到糾紛時也願意找這些大姓進行裁斷。這表明,這些大姓已經變得和當地人沒什麼兩樣,他們已經變成了雲南本地社會的凝結核。
夷經作為習慣法,內容必然是非常龐雜的。它的基礎肯定是雲南土著習慣法,但其中肯定也包括移民從漢帝國各地帶去的習慣法。無論如何,它的基礎框架肯定是立足於雲南本地的。又由於這些大姓和這些土著充分通婚,在幾代人後和土著變得沒什麼兩樣。這時候,十幾個大姓突然全部自稱來自中原,這一點就是非常可疑的了。這就如同16世紀以後,許多南粵宗族發明出北方祖先一樣。
在三國時代,對這些大姓來說,蜀漢這種流亡拜占庭政權,是不那麼令人親近的。相反,南粵士燮政權和吳越的孫吳政權,這些土豪性強的政權,是領他們感到親近的。蜀漢流亡拜占庭如果想和曹魏在北方爭霸,就必然要將南中(雲南)佔領,榨取當地的資源。所以,諸葛亮的南征就發生了。諸葛亮的南征,後來被發明成一種神話,但其中的故事明顯是站不住腳的。在這種神話裏,說得好像是諸葛亮在雲南推行仁政,收買了當地人心,通過“七擒孟獲”使當地人心悅誠服。然而,事實上,在諸葛亮南征後沒幾年,一直到蜀漢滅亡,南中大姓一直在不停造反。所以說,這些大姓並沒有因為諸葛亮的進攻就屈服於桂枝,而是一直和桂枝人進行著戰鬥。蜀漢滅亡後,他們支援西晉,與東吳爭奪交趾,付出了重大犧牲。晉朝滅吳後,他們又和晉朝進行激烈鬥爭,對晉朝進行了激烈的反抗。直到後來氐羌人在巴蜀建立成漢國後,他們才迅速向成漢投降。因此,在這些大姓看來,氐羌這樣的內亞部族,是遠比桂枝人令他們感到親近的。至於繼續希望忠於東晉的豪族,則被爨氏消滅掉了。在這之後,爨氏變成了雲南的統治者,也就是雲南事實上的君主。東晉滅掉成漢後,東晉也被南朝篡奪。南朝對雲南,更是鞭長莫及的,宋齊梁政權只能在地圖上統治雲南。這樣,爨氏就變成了真正獨立自主的政權。
在爨氏治下,經過大約兩個世紀的演化,雲南人分化成了兩個像種姓一樣的群體,分別叫白蠻和烏蠻。在今天,他們分別被看做白族和彝族的前身。白蠻在滇西比較多,烏蠻在滇東比較多。當然,這種分佈不是絕對的,在滇西也有一定數量的烏蠻、滇東也有一定數量的白蠻。白蠻是從事農耕和商業的,在雲南最大的壩子 – —蒼山洱海之間的大理壩子上,聚集著一批白蠻的商業聚落。至於烏蠻則往往住在山上,保持著遊牧習慣,保持的部落組織比較完整,戰鬥力更強。
西元570年,爨氏首領爨瓉在去世前夕,做了一件對古滇文明憲制意義非常深遠的事。他將他的王國分成兩部分,由他的長子爨翫統治白蠻、次子爨震統治烏蠻,兩個王國分別叫西爨、東爨。這樣,他就第一次將白蠻、烏蠻這兩個種姓,劃分成了兩個政治實體。後來,南詔、大理時代的憲制,就是由這兩個實體博弈、聯合形成的。這件事情之於雲南的意義,就如同查理曼帝國的三個孫子分割加洛林帝國、奠定西歐格局基礎對於歐洲的意義一樣。570年東西爨的分割,使古滇徹底走向了和大一統背道而馳的道路。加洛林帝國的分裂,也使歐洲避免了羅馬之後的又一次大一統。
(三)南詔王朝與大理王朝
隋軍入侵雲南,進行了一次掠奪性戰爭,殺害了西爨首領爨翫,在蒼山洱海之間大肆搶掠一番後撤走。西爨的權威,從此衰落了。西爨政權的基本盤,就是大理壩子一帶的白蠻。這些人做生意很厲害,他們的商人遍佈東南亞和印度,但在軍事實力不足。真正能打仗的,還是那些烏蠻武士。這個時候,蒼山洱海周圍的烏蠻,已經形成了六個王國,也就是六詔。於是,在西元652年,又一件意義深遠的事發生了。蒼洱一帶的白蠻首領張樂進求,將他的統治權讓給了六詔中最南面的蒙舍詔君主細奴邏。我們知道,白蠻是擅長農耕、商業的族群,在文化上受華夏文化影響稍大,會採用漢姓。當時在蒼洱之間,白蠻大姓氏族,主要有張、趙、楊、董、高、段。這些人將統治權交給蒙舍詔,等於是和蒙舍詔做了一筆交易:他們擁立蒙舍詔君主為王,請蒙舍詔為他們提供軍事保護,蒙舍詔也要依靠他們來統治蒼洱地區。這就奠定了白蠻公卿加上烏蠻武士的基本政治格局。這種格局,一直到古滇文明滅亡都是沒有變的。而這一格局的政治合法性,就來源於西元652年張樂進求向細奴邏的讓位。
這次讓位,是在蒼洱一帶的一根大鐵柱下完成的。當時,白蠻和烏蠻都有形形色色的原始部落信仰,每個部落拜的神都不同,白蠻稱之為“本主”。這根鐵柱,是蒼洱一帶非常重要的一處神跡。這種對柱子的信仰,應該來自原始的男根崇拜,在古代東南亞是很常見的。從這次讓位的舉行地點來看,這次讓位具有神聖的合法性,它也決定了古滇文明此後七百餘年最核心的憲制結構。
這之後大約一個世紀,蒙舍詔依靠蒼洱間白蠻大族的支持,在皮邏閣的時代統一了六詔。在748年,南詔君主皮邏閣和東爨末代首領合併,東爨歸附皮邏閣,從此南詔王室蒙氏和東爨世代聯姻。從中世紀歐洲的標準來看,這是一種典型的契約關係,並非滅人國家。南詔並沒有強奪爨氏的權力,東爨向南詔出讓權力,完全是一種自然的延續。在652年和748年這兩次讓位事件中,法統是沒有斷過的。實際權力的轉換,是靠不斷訂立契約達成的。
皮邏閣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將滇東的白蠻幾乎全部遷到滇西。這樣,以滇池為中心的滇東,就只剩下黑蠻武士了。後來,南詔又在滇池旁建立了拓東城,又叫做闡善城,也就是今天的昆明,試圖通過這個據點控制滇東的烏蠻武士。這樣就形成了烏蠻君主和白蠻公卿據有蒼洱一帶,以蒼洱之間的大理為中心控制滇西,以滇東的闡善城為中心遙制烏蠻武士的二元結構。滇東的自治武士團體,則形成了滇東三十七部,他們非常像日本歷史上的“阪東武士”。後來,皮邏閣的繼承者閣羅鳳,主要就是依靠烏蠻武士的戰鬥力和與吐蕃的盟約,兩次擊敗唐朝入侵,並向緬甸擴張,一直打到伊洛瓦底江邊。在大理城內,南詔君主雖然可以依靠自己的烏蠻身份,讓滇東烏蠻武士效忠於他。但另一方面,由於有蒼洱之間的白蠻大姓公卿存在,南詔君主又很難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集權制度。因為和南詔君主相比,那些白蠻大族是遠更熟悉蒼洱一帶的習慣法的,他們是有很強的法統性的。如果一個君主胡作非為,這些公卿就可以幹掉這個君主。
在南詔中期,果然就發生了這樣的事。君主勸龍晟胡作非為,就被大貴族王嵯巔殺掉了。按照桂枝人的理解,王嵯巔弑君,肯定是想篡位的。但王嵯巔非但沒有如此,反而先後擁立了兩個君主,忠心耿耿地輔政,他對於君權進行了有效制約。但是,王嵯巔和他立的第二個君主勸豐祐都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在王嵯巔和勸豐祐的時代,南詔大舉向東南亞擴張,兩路軍隊分別打到了緬甸和柬埔寨海岸,在緬甸的軍隊還和渡海而來的斯裏蘭卡軍隊進行了戰鬥。859年,勸豐祐的兒子世隆上臺後,殺掉了王嵯巔,又向北擴張進攻唐朝,和唐朝進行了十幾年的唐詔戰爭。為了維持戰爭,世隆進行了總體戰,下令將境內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都編入軍隊。通過不斷的瘋狂戰爭,南詔君主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君權。世隆殺掉王嵯巔,更是破壞了烏蠻君主和白蠻公卿間的權力平衡。有一個細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南詔王室是烏蠻,烏蠻的稱名方式按照氐羌習慣,不稱姓,只稱名,並採用父子聯名制的。比如,皮邏閣的繼承者就叫閣羅鳳,閣羅鳳的兒子叫鳳伽異,勸鳳祐的父親叫尋閣勸,等等。但是,世隆卻沒有繼承他父親的祐字,不叫祐世隆。事實上,這是因為勸豐祐醉心於唐朝文化,認為父子聯名法很落後,自己就將繼承自父親的“勸”字拿掉,自稱“豐祐”。受他影響,世隆直接沒有繼承“祐”字。而醉心於唐朝文化的勸豐祐,正開啟了南詔大舉擴張、建立絕對君主制的道路。所以,在勸豐祐和世隆的時代,南詔是有變成桂枝那種專制集權國家的危險的。這個節點,是古滇文明憲制史上的重大危機。
世隆擴大君權、武斷地進行總體戰。他打壓貴族,試圖建立絕對君主制後,君主的私人鄭氏跳上了臺面。鄭氏出身於唐朝俘虜,像南詔末期的權臣鄭買嗣這種人,哪怕以明朝的標準來看,都是一個“小人”,他是一個靠君主寵信晉身的人。跟那些真正的白蠻大姓比起來,他和他的家族什麼都不是。他的政權,是不可能得到蒼洱之間那些有悠久傳統的公卿的認同的。所以,鄭買嗣雖然屠殺了南詔王室,篡權建立大長和國,但根本無法進行長久統治。於是,就有白蠻大族楊幹貞依然擁立趙善政,殺光了鄭買嗣一族奪權,而後楊幹貞廢掉趙善政登基的事,這就是大天興、大義寧兩個政權的來源。
楊幹貞雖然是白蠻公卿出身,但他的奪權沒有滇東烏蠻武士的支持。他又廢掉同為公卿出身的趙善政,擅自登上皇位。他這樣做,也是不顧法統的武斷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有了西元937年,父親是白蠻公卿、母親是烏蠻武士家族的大貴族段思平,帶著滇東三十七部的軍隊打進大理城奪取政權,建立大理國的事。段思平的軍隊不光受到了滇東三十七部的支持,也受到大理城內公卿的支持,更受到了民眾的支持。他的軍隊,是在幾乎沒有遇到抵抗的情況下進入大理城的。作為一個無論是公卿還是武士全都擁護他的人物,段思平表現了高尚的政治德性。他沒有殺光楊氏一族,只讓楊幹貞出家做了和尚。在大理國初期,楊氏依然有非常大的權力。這樣做,就避免了鄭買嗣殺光蒙氏、楊幹貞又殺光鄭氏式的迴圈報復。如果段思平再殺掉楊幹貞、屠殺楊氏的話,估計從此以後滇人的政治行為,也就和桂枝人一樣沒有什麼底線了,也就沒有法統了。因此,段思平在西元937年的這次行動,是相當偉大的,它相當於英國的大憲章運動,或者日本歷史上的“承久之亂”。段思平所在的位置,承久之亂中北條政子的位置,他們各自保護了雲南和日本文明的封建自由,確立了武士集團的自治權。另一方面,段思平在進入大理城後,繼續任用白蠻大族。事實上,跟隨他起兵的人中,比如高氏、董氏,本身也是白蠻大族。這樣,白蠻公卿和烏蠻武士形成的二元格局被繼續保留下來,西元652年張樂進求和細奴邏訂立的契約得到再次承認。作為一個偉大的法統保護者和憲制維護者,段思平被怎樣高估都是不為過的。
段思平本人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將由印度傳入、在雲南本地發展出來的佛教教派滇密,與雲南憲制相結合,使雲南的憲制進一步複雜化了。在南詔後期,王室已經通過印度僧人的傳教皈依了密宗,但在當時,滇密在基層未必很普及。段思平則規定,在大理國全國境內,所有人都要禮佛,貴族子弟則要在佛寺中接受完整宗教教育後,才能出來做官。南詔的官制,是模仿唐朝制定的,當然有一些細節差別。比如,唐朝的宰相,相當於南詔的清平官。唐朝有六部,南詔則有九個部門,被叫做“九爽”。當然,南詔的官員,基本都是由世襲公卿貴族出任的。但是,南詔本身也有科舉制度。這種科舉制度,和日本平安時代的科舉一樣,是世襲制度下一種不太重要的補充。但是在世隆時代,隨著君權空前強大,以及此後鄭氏、楊氏之間無底線的仇殺,滇人很有可能走上集權之路,科舉制度也很可能成為破壞雲南憲制的工具。但是,佛教的教育制度,是和科舉制度全然不同的。在這種體制下,一個皇室或貴族子弟必須要經過寺院教育,才能獲得政治權力。這樣,就在實際上杜絕了底層文人、遊士、俘虜通過私智和親近君主暴得高位的可能性。接受佛教教育的程度,則成為一個貴族能夠獲得的世俗權力大小的衡量標準。這樣,那種模仿唐朝建立的官僚制度、那些官階、官名,也就變得只有榮譽稱號的意義了。雲南的演化路徑,就遠離了走向吏治國家的道路。
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滇密信仰的神系,和世界上其他國家都不一樣。滇密信仰阿嵯耶觀音,這個神是滇密獨有的。至於段氏皇帝,在滇密眼中則是大黑天神的化身。在滇密儀式中,段皇需要扮演以武力保護國家的大黑天神角色。通過這樣一種獨特的神系建構,滇人就和周圍的所有族群都區別了開來。在這之前,比如在爨氏和南詔的時代,滇人大概覺得自己和其他亞洲國家居民,比如唐朝人、真臘人、緬甸的驃國人沒有太本質的不同,那時的雲南是亞洲的雲南。但是,在大理國初期整個雲南社會佛教化、滇密深入社會基層後,滇人就相信自己和其他亞洲人完全不一樣了,他們是雲南的雲南人、滇的滇人、大理的大理人。這件事的意義,就如同日本南北朝時代,日本獨特的神道教理論產生,將日本定義為“神國”,從此將日本在心理上與其他亞洲國家區別開來一樣。
段思平去世的時候,已經留下了一個非常複雜的憲制結構。在大理國最初一百多年裏,楊氏的權力一直沒有被削奪,楊氏曾先後發動過兩次叛亂。段皇依靠高氏平定了兩次叛亂,此後和高氏訂立了兩個契約:首先是將滇東的善闡城作為高氏封地,由高氏世襲善闡侯,第二是讓高氏在大理城世代出任相國。權相高升泰在篡奪皇位後,僅僅過了兩年,就在1096年讓他的兒子將皇位還給段氏,這樣高段之間又訂了了第三條契約:從此之後,段氏作為大黑天神的化身,成為了永遠不可撼動的宗教、精神領袖,而高氏則負責掌管世俗權力。兩者的關係,像極了日本封建時代天皇和幕府將軍的關係。高氏還政於段氏這件事情,叫做“高氏還國”。高氏還國,本身就是一個高段之間訂立契約的過程。此後,也有高氏的人口曾出狂言,比如高智昌就說過,段皇算什麼東西,他不過是靠著我們高家才能坐回皇位,他什麼都不是。但是,他也只敢這樣說說。段高之間依靠滇密理論形成的契約,所形成的段皇的神聖權威,是沒有人敢挑戰的。高氏有再大的世俗權威,也不可能撼動段皇的地位。甚至在宗教領域,高氏也只能去信仰禪宗,而不敢涉足段皇的禁臠滇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理國的二十二任段皇中,有十任在登基後出家到滇密裏做太上皇。由於佛寺勢力是世俗權力不可侵犯的,段皇便通過這種出家的方式增進自己的宗教權威,以與高氏分庭抗禮。兩者的關係,恰似日本平安時代的天皇與藤原氏。當時,許多天皇也是靠避位出家作“法皇”的方式,和關白藤原氏形成權力平衡的。
高氏還國之後,將高氏子孫大量分封到各地,以大理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領主,這批領主被稱為“逾城派”;以昆明為中心,也形成了一批領主,被稱為“觀音派”。此後一個世紀內,高氏分封出去的領主不斷互相征戰,取代了原有的官僚體系,封建體系在雲南本部最終形成了。這些領主之間,包括逾城派和觀音派之間,以及兩派內部,主要圍繞大理的相國、昆明的善闡侯歸屬,進行了複雜的征戰、結盟,訂立了種種契約。至於小領地之間的紛爭,更是難以盡數。到1147年,滇東三十七部的烏蠻領主們和昆明的高氏善闡侯開戰。從這時候開始,雲南邊緣地區的各部落、各領主也開始紛紛建立自己的封建邦國。滇東北的滇東三十七部領主,積極向夜郎山區開拓土地;滇東南的領主,和宋朝統治下的廣西進行了巨額的貿易,輸出戰馬、換取綢緞;在滇西北,有麗江自立;在滇西和滇南,各自有百越系的金齒百夷和景隴金殿國封建割據。景隴金殿國和金齒百夷,又不斷向外擴張,在東南亞建立了更多小的封建領地。這種封建擴張,和南詔後期那種總體戰式擴張是截然不同的。我們以泰國的前身車裏王國為一個例子,看看這種擴張是如何進行的。景隴金殿國本身,就是滇南的百越系居民向南拓殖,形成的政權,他們和大理國建立了封建臣屬關係。他們中的一部分又繼續向南拓殖,在中南半島深處建立了車裏。封建體系如此擴張,就像大樹不斷長出分支一樣。如果假以時日,這個封建體系能長到什麼程度,會形成多麼複雜的憲制,將是難以想像的。這個時代,即12世紀中期以後,大理進入了自己的戰國時代。大理戰國時代,就好像室町晚期和戰國早期的日本一樣,憲制的複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路徑的可能性也變得前所未有之多。在這樣一種封建體系下,隨便一塊土地都不會有單一產權,而是會有非常複雜的產權,它可能同時會和大理的段皇、高氏相國、當地領主和佛教寺院有聯繫。要改變它的所屬權,要麼就要經過複雜的外交、要麼就要經過反復的封建戰爭。如果大理戰國時代的封建體系,在沒有外力干涉的情況下延續下去,它將變得多麼壯觀,它很可能演化出雲南自己的多國體系。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許整個東南亞和夜郎、巴蜀,都會封建化,加入雲南的封建多國體系。一個橫跨東南亞和長江上游的日本,將會誕生。
但是可惜的是,隨著蒙古人和明朝的相繼入侵,這個體系被強大的外力驟然摧毀了。蒙古人比明朝,還是要好很多的。當蒙古軍隊入侵的時候,高氏末代相國高泰祥完全可以搶先給蒙古人帶路,出賣段皇。因為他掌握著大理國的實際世俗權力,他如果投降蒙古人的話,是更有統戰價值的。但是,他卻遵守了自己的祖先,在一個多世紀前還國的時候和段皇訂立的契約,為保護段皇死而後已。他為了保護段皇,首先在大理成進行了英勇戰鬥,然後又回到自己的封地姚州繼續戰鬥,直到壯烈戰死。這是非常感人的一幕。段皇和滇西、滇南的領主,選擇了向蒙古投降。滇東由滇東三十七部形成的封建國家,則選擇了抵抗。為了鎮壓滇東的抵抗,蒙古軍從十萬人減員到兩萬人,才勉強鎮壓下去。為了徹底鎮壓這些抵抗,蒙古軍隊就花了七年時間。這比蒙古人打下襄陽之後僅僅四年,南宋就徹底滅亡,要持久得多。這是因為南宋只有一個中央朝廷,一旦消滅了那個中央朝廷,各地抵抗根本不會成太大氣候。而大理國不一樣,大理國實際上是有數以十計的封建實體在和蒙古人交涉的。他們有的選擇了戰鬥,有的選擇了合作。這種複雜的封建體系帶來的複雜外交關係,不但讓蒙古人疲於奔命,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文明。就好像你不在一個籃子裏放雞蛋,而是分幾十個籃子放雞蛋,那麼總有一些雞蛋能保存下來。滇西的段皇和滇西、滇南的封建領主,果然被蒙古人保存了下來。再加上蒙古人本身就帶有內亞的封建性,他們雖然以昆明為中心設立了雲南行省,但又在昆明分封了一個蒙古人的梁王控制滇東。經過幾代之後,梁王政權也變得比較本地化了。所以,在元末,其實古滇文明其實還是很有活力的。
(四)滅亡
蒙古梁王對段氏的忌憚,斷送了古滇文明的機會。梁王首先利用段功擊退紅巾流寇入侵,然後又謀殺了段功,使段氏和梁王之間徹底決裂。於是,明朝就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首先滅掉梁王政權,然後背信棄義地進攻大理,毀滅了古滇文明。諸滇的封建貴族低估了無產者僭主打破底線的卑劣決心,導致東亞的大洪水第一次決堤湧入內亞-東南亞邊疆走廊。明國侵略者將滇人正統王室流放到武昌和雁門的衛所,切斷了他們和祖國的聯繫,系統地消滅滇文化,“在官之典籍,在民之簡編,全付之一炬”,甚至平毀了段氏發源的文閣村和蓮花山,焚燒了大不列滇(The Great Diantnam)古典時代的遺產五華樓。“朱明暴政,傅沐殄虐,滅盡南史,片紙皆灰。屠胄戮僧,焚寺碟碑,斷山絕坎,逐殺流潛,千古劫難!”
二、明清時代的雲南新共同體
(一)麓川戰爭與沙普戰爭
明國佔領雲南後實行的制度是,在將雲南納入帝國州縣、衛所體系的同時,又在昆明分封了黔國公沐氏。這種制度,首先就使明國在滇統治機構帶有二元色彩。沐氏的始祖沐英雖然是侵滇明軍將領,但等到幾代人之後,沐氏家族在雲南本地的既得利益越來越多。所以,他們雖然仍然會依靠自己的特權繼續壓榨滇人,但有時候也會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阻撓朱明中央對雲南的掠奪。此外,不但明國治滇機構帶有二元性,明國在雲南的整個統治結構也是二元的。這種二元性,比前面一種重要得多。一方面,明國雖然在雲南設立了一大批州縣,並設置了一大堆重屋疊架的統治機構。另一方面,對大理戰國時代以來生長出來的那些封建領主,明國也無力一個個消滅,對很多領主只能進行“冊封”,維持一種表面的統治。為了維持對領主表面上的宗主權,明國設置了“三宣六慰體制”,在雲南和相當於今天緬甸、老撾、泰國境內的各領主之上,設立了南甸、幹崖、隴川三個宣撫司,還有車裏、緬甸、木邦、八百大甸、孟養、老撾六個宣慰司。三宣六慰的長官名義上是明國官員,實際上是由土司世襲的。事實上,緬甸、老撾、泰國的那些領主,大多數本來就是古滇封建體系的一員。明國雖然消滅了大理國,但如果要將整個封建體系消滅,勢必要消滅掉所有領主,難度非常大。所以,明國只好機會主義地採取了這種體制。這樣,雲南實際上就被分成了“明屬滇尼亞”和“封建滇尼亞”兩部分,兩者的憲制結構在根本上對立。在14 – 17世紀之間,明屬滇尼亞掌握的人口,主要是帝國軍人和強制移民,其中江淮人占多數,他們的背後是大一統帝國的行政機構和沐王府,主要龜縮在明國劃定的府城、縣城和屯田中。而封建滇尼亞,則由封建領主構成,他們是古滇遺留下來的多國封建體系。在這兩個多世紀裏,前者一直試圖用各種手段削弱後者,而後者則不斷反抗,最終推翻了明國對滇的統治,並形成了當代東南亞多國體系的前身。
兩者的第一次衝突,是15世紀中期的麓川戰爭。這次戰爭非常慘烈,前後打了三次。明帝國不得不求助於三宣六慰體制下的各領主,才用恐怖的大屠殺消滅掉滇西麓川領主思氏。打完這場戰爭後,明國對中南半島微弱的控制開始瓦解。那些在戰爭中壯大的領主,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國家。首先,阿瓦領主壯大起來,征服了中南半島上的大批領主,演變成為緬甸。到16世紀,緬甸又和葡萄牙人結盟,向東擴張,使被打擊的領主也紛紛武裝起來、形成國家組織,促成了泰國和老撾的出現;此外,緬甸又向雲南進攻,在明緬戰爭中沉重打擊了明屬滇尼亞的吏治國家機器。持續到17世紀初的明緬戰爭,使明屬滇尼亞的編戶齊民減少了六成。到這時,明屬滇尼亞事實上已經搖搖欲墜。從1630年代開始,雲南本土的領主普名聲、沙定洲發起反明戰爭,在1645年攻陷昆明,基本消滅了明屬滇尼亞,將明國治滇官僚機構和沐王府連根拔起。這樣,到17世紀中葉,明國強加在滇尼亞的一切幾乎都消失了,雲南封建體系大獲全勝。
然而不幸的是,退到滇西的明國殘黨,勾結流竄蜀、黔的張獻忠流寇餘部孫可望、李定國,利用食人族流寇大軍鎮壓了這次光復戰爭。流寇一路屠殺,以南明永曆帝為花瓶,將統治經濟和集體農莊強加給雲南,實行抗清總體戰。不久後,滿清軍隊又進入雲南,消滅流寇,再進行了一次屠殺。隨後,被分得雲南的滿清平西王吳三桂,又以雲南為根據地,和清國拉鋸八年。等到康熙帝的軍隊進入雲南時,明屬滇尼亞遺留下來的那些編戶齊民和軍戶,實際上已經被基本消滅了,殘留下來的人口可能不到雲南的一成。
(二)湘贛移民與新滇語
對於雲南來說,流寇、吳三桂和清國都是很殘酷的侵略者,雖然三者經濟統制的烈度不斷降低,但三者都對雲南的封建領主大肆鎮壓。到1720年代,雍正帝和鄂爾泰主導的“改土歸流”,將這種鎮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比如,長期在滇藏之間活動的麗江,就是在這次“改土歸流”中被消滅的。所謂的“改土歸流”,就是通過各種手段消滅由土司統治的封建領地,代之以帝國流官控制的州縣。然而就算如此,終清一代,雲南土司從沒有被徹底消滅,還有數以十計的領主被保留下來。與此同時,在18到19世紀中葉之間,還有兩股新力量進入雲南。第一股,是清代入滇的移民,以湘人、贛人為主。這些移民不同於明國的強制移民,多是自發移民,從事商業、農業的人很多。他們雖然主要來自非“官話”區,但用所謂的“西南官話”,也就是上江語為共同語言。他們的人口在雲南的帝國州縣區大量增長,漸漸超過了土司領地的人口,也使上江語變成雲南各族群用以交流的共同語。這種語言逐漸與同為上江話的蜀語產生區別,形成了今天的”雲南話”,也就是新的滇語。
此外,伊斯蘭教在雲南也大量傳播開來。伊斯蘭教是從內亞進入雲南的。我們知道,在古滇文明時代,雲南一直有著濃烈的內亞色彩,通過“身毒道”和“藏彝走廊”與內亞相連。在明國治下,雲南的伊斯蘭教遭到了沉重打擊。到16世紀,雲南大部分穆斯林的信仰已經很淡了。但是,在16世紀晚期,隨著明帝國統治能力衰退,伊斯蘭教開始在東亞復興,首先在陝西形成了東亞穆斯林的“經堂”組織。經堂組織的前身,是阿拉伯世界的經文學校。這種組織進入東亞之後,吸收了儒家書院的組織形式,在整個東亞的穆斯林世界中傳播開來。到17世紀後期,雲南本地的經堂也建立起來。經堂制度為雲南穆斯林提供了學習阿拉伯文、波斯文宗教典籍的場所,使正常的宗教組織與活動全面復活。到19世紀中葉,雲南的700萬人口中,穆斯林達到80萬人。有的穆斯林已經到過土耳其和埃及學習教法,並去過新加坡學習英國科技,與中東的伊斯蘭教組織連為一體。而這時,林則徐、魏源這些人剛剛進行所謂的“開眼看世界”。對移民的會黨、宗族和穆斯林的宗教組織在19世紀中葉不斷壯大,清帝國非常恐懼。為了削弱兩者,滿清官吏不斷挑動回“漢”械鬥、互相屠殺,從而坐收漁人之利。這種政策,就是所謂的“漢強則助漢以殺回,回強則助回以殺漢”。
在這種形勢下,雲南的封建領主、移民和穆斯林都成為清帝國暴政的犧牲品。清帝國本以為用這種方法,就能在雲南維持長治久安。然而,一場起義將雲南的這三個群體團結了起來。這場戰爭與一個偉人有關,他就是杜文秀。
(三)杜文秀起義與近代雲南共同體
在杜文秀起兵前夜,整個雲南在清帝國挑動滇人自相殘殺的政策下,已經陷入了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大規模械鬥。1856年杜文秀起兵時,追隨他的大都是想對非穆斯林進行報復的穆斯林教眾。然而,杜文秀攻佔大理後,卻宣佈寬恕大理的所有居民,建立了雲南各族共治的政權。杜文秀麾下的將領和軍人,涵蓋了雲南的所有族群。對於穆斯林來說,杜文秀是蘇丹;對於移民來說,杜文秀是儒家意義上的皇帝;對於白族、傣族、彝族的封建領主來說,杜文秀是總領主。杜文秀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首先,他的家人基本都在之前的械鬥中,被非穆斯林屠殺了。首先,在多年的械鬥中,雲南各族群間已經形成了血海深仇。然而,杜文秀第一次指出,這一切的禍源都是清帝國,雲南的各族群都是受害者。要想結束這種狀態,只有推翻清帝國在雲南的統治。杜文秀在1863年發佈的《討滿清檄》,無疑是雲南各族群在19世紀共同宣佈的《獨立宣言》。我們來看一看這篇文章:
“總統兵馬大元帥杜,為興師五路,收復全滇,除殘暴以安良善事:竊思滇南一省,回漢夷三教雜處,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嘗有畛域之分?慨自滿清僭位以來,虐我人民二百年餘於茲矣。妖官偏袒為計,石羊起釁,池魚皆殃;強者逞鴟張之威,弱者無鼠竄之地。爾時百姓危若倒懸,可惡妖官猶安然高枕,置蒼生於不問,棄黎庶其如遺。甚至漢強則助漢以殺回,回強則助回以殺漢,民不聊生,人心思亂。
“本帥目擊時艱,念關民瘼,不忍無辜之回為漢所殺,更不忍無辜之漢被回所殺。爰舉義師,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漢。至大事之圖成,惟天命之是聽。無知妖官窮謀詭計,倒行逆施,殺協鎮者封以協鎮,殺都郵者授以都郵。高明退身,庸愚墮計。始也助漢以殺回,今也助回以殺漢;繼也助漢以殺漢,今則助回以殺回。鴻溝之血未幹,烏合之師突至;妄思螳臂以當車,奚啻雞卵之擊石。
“今者小計略施,月奏三捷;雄師半出,功收數城。然妖官未除,禍根猶在;全滇不取,億兆難安。況乎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用是師興虎隊,將選龍驤,糧運千倉,餉籌百萬,槍炮在其前,弓弩列於後,長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並進,效一怒而安民。劍戟橫空,勝氣騰雲,千裏旌旗蔽日,威鎮雷動九天。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凡爾城鄉紳耆,遠近士民,達務知時,不乏俊傑,轉禍為福,定有同心。或率眾而來歸,或開門而效順,定當量才而錄用,不別戶而分門。自此烽煙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有歸,共成王霸之業。豈不樂哉!豈不快哉!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行將後悔。況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縱背城航海,亦奚以為!檄文到日,凜遵勿違!此檄。”
如果說,在此之前,雲南還沒有在政治上形成一個完整的共同體,在此之後,雲南已經具備了民族國家的雛形。這也是為什麼杜文秀的軍隊,能在短短幾年內能席捲除昆明外幾乎雲南全境的原因。在杜文秀出現之後,之前雲南內部的宗教和族群衝突,就轉化成了雲南各族群對清帝國的一致反抗。站在清帝國一邊,和杜文秀對抗的滇人將領,也是既有穆斯林、又有非穆斯林,而這些人在滇人當中,實際上只有一小部分。從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一次滇人的獨立戰爭。在這次戰爭的最後階段,還曾有一個名叫劉道衡的杜文秀政權官員出使英國,向英國提出將全滇獻給維多利亞女王,請英軍支援滇人抗清。杜文秀起義雖然被經過洋務運動的清軍,用優勢武器鎮壓了。杜文秀在大理陷落前,將自己的生命交給清軍,希望清軍放過城裏的百姓,但清軍卻背信棄義地進行了屠城。這場戰爭雖然在1873年失敗,但卻表明滇人不但已經成為一個能夠集體進行政治決斷的共同體,更有進行國際外交的能力。到20世紀初,隨著西方傳來的民族主義思潮在雲南發酵,清帝國在雲南的統治進入了倒計時。
三、近代雲南民族主義
(一)海外雲南民族主義
由於有過杜文秀的獨立戰爭,因此,將整個雲南作為一個共同體,實行民族獨立,成為一種必然會出現的思潮。20世紀初,滇越鐵路通車,以法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向雲南大舉輸入教會和物質文明。此外,大批雲南留學生赴日,他們接觸到了西式民族主義和日本泛亞主義思潮。1906年,同盟會雲南支部機關刊《雲南》創刊,提出了雲南獨立的主張。雲南獨立主義與日本泛亞主義的淵源很深,它在強調反滿的同時,也希望雲南獨立運動能夠帶動緬甸、越南掙脫英法的統治。在此前提下,滇獨運動又分成兩派,一派主張直追南詔大理歷史、將20世紀滇人認定為古滇後人,還有一派則認為雲南人的主體是“漢人”,將自己的祖先定義為明國佔領雲南後入滇的移民,稱明國對雲南的統治是“開化”。在這兩種思路下,《雲南》雜誌中有的文章認為雲南獨立後將成為“亞洲英吉利”,成為世界上有數的富國、強國之一,有的文章則提出雲南獨立後將變成中國一個有自治權的省。這樣,從事滇獨運動的青年就不但與日本泛亞主義有聯繫,還和孫文的同盟會關係密切。事實上,許多青年的身上同時具有上述兩種思潮,並無明確思想。不過,他們的行動力是非常強的。比如,最著名的滇獨青年張成清,有一半緬甸血統。1908年,他在緬甸成立“雲南死絕會”,宣佈雲南和清廷脫離關係,並將幫助越南、緬甸、印度獨立,最後被英緬政府處決。還有的人則在滇緬邊境組織遊擊隊,進行了長期戰鬥。在這種背景下,這些青年也滲透到了清國在雲南成立的新軍中,唐繼堯就是這些軍中滇獨青年的領袖。事實上,1911年雲南的“重九獨立戰爭”,就是由這些軍官策劃、發動的。滇軍在獨立戰爭中的總指揮蔡鍔,是在這些青年軍官完成策劃後,才被籠絡的。蔡鍔是湘人,他因為是梁啟超的學生、又在軍中名望較高,因此被這些人請了出來。蔡鍔本人,也許未必有強烈的滇獨思想,但他依然被這些青年視為合作對象。從這一點就能看出,這些青年確實是上述兩種民族主義的混合體,他們雖然都愛雲南,但對雲南民族的建構到底是否應該與中國分離,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觀點。事實上,蔡鍔本人也是這樣一個二元的湖湘民族主義者。這種二元愛國者,在全世界各民族形成的初期,都是常見的。
(二)從雙重民族主義到”大雲南主義”
1911年推翻清帝國統治後,雲南雖然在第二年加入了中華民國,但以蔡鍔為首的滇軍仍然控制著雲南,民國史上有名的滇系浮出了水面。當時,與雲南相鄰的貴州相對弱小,四川則很快就成為各種勢力割據的戰場,師從日本的滇系實力比黔、蜀強很多。如前所述,滇系的領袖都是既支持雲南獨立、又對中國態度曖昧的二元愛國者。因此,他們既希望保持雲南自立、又有干涉黔、蜀乃至爭霸中國的野心。加之蔡鍔是梁啟超的學生,梁啟超便希望滇系成為他在北京國會中的進步黨的週邊組織,這就使情況更加複雜起來。因此,1911年之後,雲南立刻就捲入黔、蜀的戰爭泥潭中。然而,無論如何,滇系都有最基本的底線。那就是,當中華民國變質成另一個清帝國,試圖取消各“省”自治時,他們一定會奮起維護。1915年底,隨著袁世凱稱帝,這樣的事情果然發生了,蔡鍔隨即在雲南起兵獨立,引起諸南連鎖反應,在半年後粉碎了袁世凱的中華帝國。在此期間,雲南與日本曾有過接觸,日本甚至有過承認雲南為獨立國的打算。這次獨立戰爭的起因,雖然有進步黨試圖利用滇系逼宮的因素,也有滇系試圖維護北京政權“國體”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是滇系二元愛國主義的直接表現。雲南甚至曾與日本進行過聯合,來反對袁世凱的中華帝國。
袁世凱死後不久,蔡鍔也去世了。唐繼堯接手滇系後,投入了對貴州、四川的侵略中,這就是1916年開始的所謂“大西南戰爭”,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大上江戰爭”。唐繼堯發動戰爭的思想動機,一是由雲南愛國主義發展而來的“大雲南主義”,二是滇系爭霸上江乃至“爭霸中國”的野心。事實上,這是二元愛國主義擴展到極端的產物。姑且不論,這種戰爭有建立一個以雲南為核心的大一統中國的可能,它還會將雲南拉入瘋狂的總體戰中,將雲南民眾的財產投入到無意義的對外侵略,損害雲南土豪的利益。民族建構,如果脫離了保護土豪的因素,便會產生嚴重的負面效果。這場戰爭,以1920年唐繼堯在重慶舉行盛大的入城式為頂點。這一刻,他成為了雲南的拿破崙。而雲南因為連年戰爭,已經陷入了民窮財盡的境地,唐繼堯則借助戰爭,逐步建立他的獨裁權力,開始處決他過去的戰友。此後,隨著四川全境對唐繼堯發動反抗,滇系的擴張開始退潮。1921年,雲南本土發生了滇軍將領顧品珍起義,這次起義如同施陶芬貝格起義一樣悲壯。顧品珍代表雲南本地土豪的利益,一度控制昆明,試圖將唐繼堯趕下臺,但功敗垂成,被唐繼堯殺害。這之後,唐繼堯又繼續對外擴張,並東擴戰線,在1924年發動了對廣西的入侵,遭到慘敗,新桂系也在這次戰爭中誕生。同一年,國民黨和共產國際在廣州聯合,開始顛覆遠東國際秩序。經過這次慘敗,唐繼堯的頭腦清醒不少。他放棄了對外擴張,對內致力於鎮壓共產國際勢力。然而,他又試圖加強軍事獨裁,撤銷各部番號,加強自己的親衛隊。這種情況下,本土軍官遂在1927年發動“二六兵變”,廢黜唐繼堯,實行保境安民的路線,不再進行軍事擴張和獨裁政治。隨後,滇軍諸將權力鬥爭,龍雲上臺。
(三)雲南單邊愛國主義
與龍雲接手滇系同時,國民黨席捲了東亞大陸。龍雲並沒有選擇與蔣介石開戰,而是掛上青天白日旗,名義上服從國民黨,實際上依然維持著雲南的自立。在蔣介石看來,雲南當然是國民黨治下的一個省。但在龍雲看來,雲南無疑是一個自立的政治實體。值得注意的是,龍雲是彝人,但他與雲南其他族群出身的滇系將領一樣認同雲南、保衛雲南。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雲南各族群在此時已是一個非常堅實的共同體了。在1930年第二次滇桂戰爭失敗後,龍雲不再對外擴張,對內則推行地方自治、實行軍國民主義訓練民兵,並任用繆雲臺制定經濟政策,在政府扶植業下發展金融業、進行工業化。到1935年,雲南境內的共產黨只剩下六七個人,等同於全滅,和蔣介石形成了鮮明對比。假以時日,雲南會完成自己的明治維新。然而,也就在這一年,蔣介石借剿共為名派中央軍控制了黔、滇,並威脅龍雲與之同盟。龍雲鑒於兩者實力差距懸殊,只好同意。雲南隨後被拖入蔣介石的反日戰爭。
對日戰爭中,雲南雖有部分部隊被迫出滇參戰,但雲南仍對蔣介石進行了盡可能的抵制。比如,汪精衛投日時曾路過雲南,若無龍雲默許,他不可能逃出。此後,龍雲和汪精衛之間長期進行著秘密聯絡。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龍雲曾一度計畫和山西閻錫山、四川聯合反蔣、對日和談。此外,龍雲奉行“朋友的敵人就是朋友”這種原則,包容共產黨,埋下了隱患。1942年日軍從緬甸攻入滇西後,還有滇西土司計畫聯合日本,成立“南詔聯邦合眾國”,但沒有得到日本回應。此後,雖然蔣介石的大批中央軍開入雲南,在滇西和日軍作戰,但滇軍並沒有積極參戰。在滇越邊境,滇日兩軍可謂相安無事。可以說,龍雲和蔣介石在二戰中的所謂聯盟,類似弗朗哥與希特勒的聯盟。弗朗哥的西班牙雖然曾派兵幫助希特勒進攻蘇聯,但並沒有全力投入二戰。可以看出來,到這時候,滇人已經對蔣介石的抗日宣傳很不感冒,之前的二元愛國主義,正在變為一元愛國主義。對於龍雲的這種態度,蔣介石必欲處之而後快。1945年,二戰剛一結束,蔣介石就讓中央軍發動“五華山政變”,推翻了龍雲。
此後,盧漢接手的滇系,已經深深受制於蔣介石,缺乏自主力量。為了和蔣介石對抗,盧漢繼續奉包容了大批共黨。這一政策的出現,固然有龍雲、盧漢對共黨統戰政策認識不清和機會主義等因素,但歸根到底,還是蔣介石逼出來的,首要責任當然在蔣介石。國民黨的歷史使命,便是在為共黨掃清一切道路後,被共黨打敗。其實,盧漢並不是真心喜歡共黨的。1949年底,當共黨快要打到雲南的時候,盧漢曾試圖和美國進行交易,提出雲南宣佈獨立、由美國派兵援滇的計畫,但被二戰後採取儘量避免捲入戰爭的美國拒絕。隨後,盧漢便為自保,向共黨投降。雲南之所以有這樣的命運,國際局勢的演化也是重要原因,但盧漢的機會主義短視和明哲保身恐怕是更大的因素。如果盧漢不是長期與共黨暗中合作,直到1949年底才和美國接洽,雲南很可能就不會面臨這種命運了。
四、被奴役的滇民族
(一)中國人對當代滇人製造的種族滅絕暴行
1949年,滇系領袖盧漢與共產中國達成外交協議。盧漢宣佈”起義”脫離中華民國,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雲南需享有高度自治權。但是共軍入滇後撕毀了與盧漢的協議,先後在各次”運動”中屠殺了近100萬以上的雲南人。
從1950年到1953年,中國對雲南進行了第一次屠殺,第一次屠殺的遇害對象死者大約13萬人以上,中國人污蔑這些遇害者是“土匪”,但這些森實際身份都是原雲南軍官、教師、地主、民兵領袖等,他們打著”滇人治滇”的旗號反抗共產中國,慘遭鎮壓,類似波蘭卡廷森林的遇害者。
從1956年到1961年,中國人對雲南製造了種族滅絕式饑荒。猶如史達林對烏克蘭人做的那樣。總共餓死近80萬雲南人。
從1966到1976年,中國人又對雲南人進行了大迫害,打死了5萬左右的雲南人,同時將15萬左右的雲南人打成殘疾。
今天的滇人和東突厥斯坦人、藏人一樣,淪為了中國的奴隸。
(二)海外滇人孤軍的反共戰爭
雖然1949年以後雲南本土被共產中國佔領,但一批雲南孤軍依然不願意放棄抵抗,他們流亡到東南亞。1950年代,他們在李彌將軍的指揮下一度控制了緬北。但蔣介石卻對李彌極不放心,將李彌召回臺灣軟禁。不久後,國民黨徹底拋棄了這支孤軍,緬甸也和共產中國勾結,對孤軍進行夾擊。孤軍中的雲南裔官兵不願意投降,向段希文將軍的帶領下泰國流亡,最後在1980年代,通過幫泰國消滅紅色高棉殘黨和苗共獲得了泰國公民權。在這幾十年裏,不斷有從雲南逃出的滇人被孤軍收容。今天的泰國美斯樂,依然生活著孤軍和他們的後裔。這些孤軍,和流亡巴黎的幾萬烏克蘭愛國者有什麼區別?李彌、段希文的遠征,就是雲南版的彼得留拉“冬征”。這段“亞細亞孤兒”的故事,是雲南當代史上最悲壯和感人的一幕。
這只滇軍配合朝鮮戰爭的美軍,在滇國西部跟陳賡所率領的中共進行了長期的戰鬥。由於他們的戰爭,五十年代的緬甸、泰國各國才得到了緩衝時間。本來五十年代初期的緬甸和泰國自身的軍備還是治安軍的水準,是十九世紀的裝備。雖然美國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準備給他們換裝,但是換裝是需要時間的。就像今天的烏克蘭一樣,今天的烏克蘭在蘇聯解體、自己解除了武裝以後,就遭到了俄羅斯的侵略,而美國雖然是要像援助波蘭一樣援助它,但是援助、重新換裝、重整軍備的過程至少需要五到十年。如果在這五到十年之間俄羅斯突然發動入侵的話,烏克蘭人是很難有抵抗力的。蔣介石政權之所以垮得這麼快,也是因為類似的原因。而滇軍的抵抗至少是給緬甸和泰國贏得了長達十年的換裝時間。
等到六十年代中葉,吳庭豔政權和東南亞條約的泰國政權都已經換裝完畢,自己具備了一定的抵抗能力,這時滇軍就不再重要了,美國和福摩薩對滇軍的支持也就告一段落。這時,絕對主義派的滇人有很多都接受了福摩薩方面的退休金,搬到了福摩薩去住。而本土派和封建主義的滇人則相信,他們的根在滇緬邊境上,他們不一定需要旁人的援助。而且離開自己的家鄉,也就退出了本地的封建體系,也就放棄了自己的複國大業,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划算的。因此,他們寧願失去援助,也要在邊界地帶堅持下來。這些人一直堅持到現在。
(三)滇民族的未來希望
毛澤東在企圖背叛赫魯雪夫建立自己的獨立體系又失敗、不得不投入美國體系以後,中共放棄了自己原先的蘇聯牌的國際主義,穿上了蔣介石留下的靴子,以東亞奧斯曼主義的繼承者自居,相應地就反映在它的外交政策上。它在外交上企圖把從哥斯大黎加、馬來西亞直到夏威夷、南非和美國的原先在常凱申控制之下的海外組織一一攻陷的時候,類似的戰役也在滇緬邊境展開了。屬於中華民國系的土司和領主像三藩市、夏威夷和馬來西亞的堂口一樣,有的被中共攻破了,有的像滯臺國民黨一樣投降了,變成中國推行帝國主義擴張的一個白手套。然而原先屬於封建主義體系的滇國土司和領主,在這場鬥爭當中始終堅持了自己的傳統。
由於滇緬邊境的複雜形勢,無論是以前的國民黨還是現在的中共,都只能控制封建網中的一小部分,而從內亞穆斯林世界到東南亞穆斯林世界之間的交通網絡,隨著中共在跟西方國家打交道、推行改開白手套這三十年間,又有了新的成長,因此,現在的滇緬邊境可以說佈滿了很多小小的杜文秀。原先早在中古時代就留下的那些段氏、高氏的封建領主的繼承人並沒有全部走掉,他們現在還在那一帶,蒙古帝國時期重新滲入的內亞領主、穆斯林團體之類的仍然在成長,而改革開放三十年產生出來的新的商團也在茁壯成長。這三代不同的封建滇人的體系和國民黨系、中共系的中國殖民主義體系縱橫交錯,在東南亞的中流砥柱正在推行一場複雜的博弈。這場博弈的下麵,就是內亞穆斯林通過東南亞運送難民和武器的地下鐵道和東南亞土豪向香港運送毒品和越南大米之類的走私物品的管道。這兩條管道的存在,就說明瞭今天滇國境內封建生態的複雜性。
在鄧小平時代,共黨不敢跟西方國家正面衝突的時代,它就滿足於控制以軍隊、員警和國有企業這個表面上的體系,然而這個體系即使是在滇國境內,也只能夠佔據一小部分生態。而以改開名義崛起的各路土豪,他們主要就是依靠跟東南亞和內亞的國際交通網才能發財致富的,因此他們必然要跟原先滇國的三代封建領主以及新崛起的內亞和東南亞網路發生密切聯繫。當然他們當中有大批匪諜,但是也有原有的封建體系和滇族愛國者的很多勢力。
隨著中國跟西方國家再次決裂,決裂必然要反映到滇國內部的政治生態,也就是說,中國能夠控制的那些體系必然會跟滇人原先的和新興的封建體系之間為了爭奪地下網路和生態而進行殊死決戰。這場戰鬥是殘酷的,經常會以比如說某一位滇國的愛國土司或者是匪諜土司被他們的敵對派系襲擊、以至於滅門為代價,但是這場鬥爭對於保護內亞和東南亞的土豪勢力、保護滇國本身的獨立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說那種滅門慘案在1990年代後期、在江澤民時代就是經常發生的話,那麼隨著中國的殖民帝國和西方國家正式決裂、也就同時喪失了綏靖和收買東南亞和內亞土豪勢力的主要支援的政治進程不斷展開,滇國原有的土豪必然會在留在內亞和東南亞的網路支持之下,為了爭奪資源和生態,跟中國恐怖分子的殖民勢力展開更加殘酷的生死決鬥。
在中共統治的雲南本土,雖然也遭遇了和東亞內陸各地同樣的命運,先是被格式化,隨後又在該開中面臨社會原子化的危險。然而,從幾個現象來看,雲南是非常有希望的,本土的力量依然保存得很好。一直到1950年代後期,雲南依然有武裝反抗。而與此同時,大批中國河南人寧肯餓死也不敢衝擊糧倉。在文革時,不但有大批雲南人去東南亞投靠孤軍,雲南本土的造反派也非常強勢,顯示出了一些實質運動的樣子。就算在文革末期,雲南本土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組織依然在活動,沙甸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展開的。1990年代的小洪水中,雲南形成了所謂的“毒販村”,擁有極強大的武裝。直到今天,雲南依然會發生富有村這樣的事件。昆明火車站事件時,沙甸的穆斯林也沒有和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同流合污,拒絕收留這些人。與此相對照,他們在文革時卻接納而來的雲南本土造反派。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內陸諸南中,只有滇國的人口總量不是外流的。這一切表明,雲南的未來絕不是沒有希望的、雲南的本土共同體是非常強大的。而這種局面,就是雲南悠久歷史演化而成的結果。
在著名歷史學家劉仲敬的幫助下,有人寫出了雲南民族主義史觀的《大不列滇史》,當代雲南民族主義者稱呼雲南為“大不列滇”,劉仲敬認為未來雲南和廣東必然是較早脫離中國的國家。他認為:”未來的諸夏愛國者完全有理由像他們在蔡松坡時代一樣,把希望寄託在滇國愛國者的身上。”